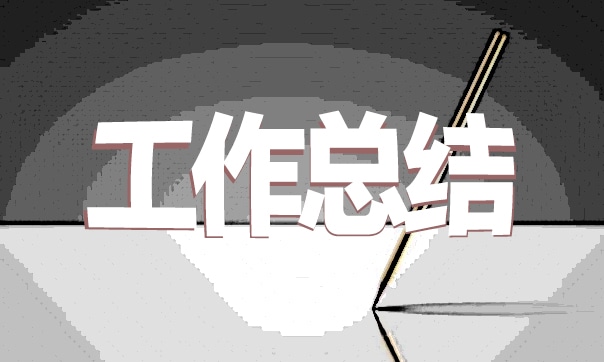真爱无言-读者
我家在新区的东边,周围房子很少。隔壁只有一座空着的平房。很安静。2000——2002年我因病成天呆在床上。心情极度灰色。
窗外。夕阳把整个院落及远处的山峦渲染上一层橘红的色彩,我想象着树上的叶子一片片零落,我就开始一点点地绝望了起来。我将自己埋进了预设的死亡里面寂然无声,也怕听到来自外界的任何声音。哪怕是轻微的一点点。
家里也因我的病而显得死气沉沉,电视也没开过。就连三四岁的女儿也让爱人教育得声音小小地说话,脚步轻轻地走路。
我,沉浸无边的静寂中。日复一日,彻夜无眠。
一日傍晚,隔壁忽传来了一嗓子秦腔,我脆弱的神经几乎被这响亮的声音击碎。我愤怒地问正在打毛衣的妻子——是谁在唱?妻子说是外地来的民工,租了隔壁的房子住着。已一年多与外界隔绝了的我,乍听到这声音心里无比的烦躁。
妻子放下手中的毛衣,给我倒了杯水说:“他们也不易,也就在这点时间里乐一乐了。一天够辛苦的。”
她侧耳听了会又说:“你听,是你最爱听的《祭灯》呢。”
我好奇地仔细听了下,还真是《祭灯》。唱的还行,嗓子沙哑着,悒悒郁郁的腔调很有秦腔大师焦晓春的韵味。
听着听着我心里的烦躁慢慢地退却了。思绪飘出窗外,己然飘过剥落的栈道,飘过巴山蜀水,飘到了我的童年。
儿时的乡下每年开春都要唱社戏。扎着羊角小辫的我骑在爷爷的肩上,啃咬着一串冰糖葫芦。在锣鼓声嘎然而止时随着一声:“后帐里转来……”一个人踏着鼓点颤巍巍地迈着疲惫的步子徐徐从帘子后面走了出来。刹时间整个戏场一下地鸦雀无声。兜售零食的小商贩也停住了忙碌的脚步,不再在人群里穿梭。
爷爷吧嗒着烟斗对我说:这人——就是诸葛孔明。
于是我记住了这张泛着暗黄色的面容,记住了那身着皂衣手执宝剑披头散发向荧荧如豆的七盏油灯下拜的瘦弱身躯,那为汉室向苍天祈祷着欲借几载生命的身影。还有那板胡悒悒郁郁的腔调。
——这出戏就是《祭灯》。
后来慢慢从零零星星的传说中得知诸葛亮平时是不拿宝剑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柄他妻子赠他的羽扇,头顶的是一方纶巾。长大上了初中,读到《出师表》的古文。当读到:“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那悒悒郁郁的腔调又一次在心头响起……
我喜欢《祭灯》这出戏,是因为它里面有着生命的厚重和人生的一种感动。
隔壁的《祭灯》唱完了好久,我的思绪才回到了床前。床前,妻子正蹲着给我捏着毫无知觉的双腿。
那夜,我破天荒地竟然没有失眠,睡得很好。我甚至梦到了小时侯放牧过的羊群。山坡上长满着鲜嫩的小草。那草的绿色映照着我的整个梦境,直至染绿了我第二天的心情。妻子和年迈的母亲高兴的不得了。
自那以后,每到傍晚,妻子就把我扶着靠坐在床头。静候着隔壁传来那在八百里秦川上流淌而来的秦腔。而隔壁总会准时地“开戏”。《下河东》、《铡美案》、《五典坡》、《周仁回府》等等秦腔名剧中的唱段一一唱来。我病中的日子也因秦腔而争添了许多生命的颜色。
妻子陪着我一夜一夜地听着。令我惊异的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唱段很少有重复的。我被这秦腔的粗犷和洒脱所感染,病也竟然有了一点点起色。我已能在屋里让人扶着慢慢走几步了。电视也打开让女儿看动画片了。家里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深秋的个傍晚,我仍旧靠在床头,等待着隔壁传来秦腔那激情迸溅的声音。可隔壁静悄悄地再没有秦腔唱起。我无比的失落,爱人陪我静静地坐着。直至深夜。
此后的日子里隔壁再也没有传来一点声音。我心里空落落的。直到初冬落下第一场雪。爱人到她那不景气的厂子上班了。屋里的炉子烧的很暖和。我在床上拿着一本书随意地翻着。大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母亲开了门,进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他提着只很大的提包,走起路来腿有点瘸。他径直来到了我的卧室。在我诧异的眼神里,他腼腆地笑了笑。问我:“您身体好些了吗?我就是隔壁唱秦腔的人。”
这,在他一开口我就听出来了。听了一个多月的秦腔,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只是我们没有见过面而已。我热情地让他坐,他连连摆着手说:“不了不了,我那婆姨在隔壁捆铺盖,立马就要走了。”
我问他最近咋不唱了?他说前一阵子摔伤了。
他点燃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粗重地将吸进去的烟吐了出来。
他在提包里掏出了好多盘秦腔的光盘,说是给我的。望着茫然的我他沉默了一会给我讲了一故事:
一个人和妻子赌气离家出门打工,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个地方,租了一间房子。
一天他哼着秦腔,他哼完了一段时才发现门口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在听。就在他愣神的刹那,那女人说话了,问他:您会唱《祭灯》吗?
他当时自豪地说:会啊!还会好多呢!
那女人显得很激动。问他能不能在每天傍晚大着声唱一段?她的语气近似于乞求。他开玩笑地说,唱一段10块钱。那女人爽快地拿出了一叠钱给他。钱的面额大小不一,最大的是五元的。那女人的体温在每张钱上,一如春天的阳光所发出的温度,祥和而温馨。
他数完第二遍之后就答应了。她只要求前几天唱《祭灯》,以后就由他唱。他为自己意外轻易地得到了300元而兴奋着,每天傍晚他就卖力地唱着。
直到有一天他在另一个建筑工地上意外地碰到了那个女人。当时那女人正和几个男人一起抬着一块楼板。她纤小的身材在杠子下显得异常柔弱。他向别人问起这个女人的来历,当地的个民工叹了口气说,她丈夫已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了。他听了后就想起了在他赌气离家时的妻子也生着病。他神思恍惚地上了脚手架……
我没听完就已泪流满面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